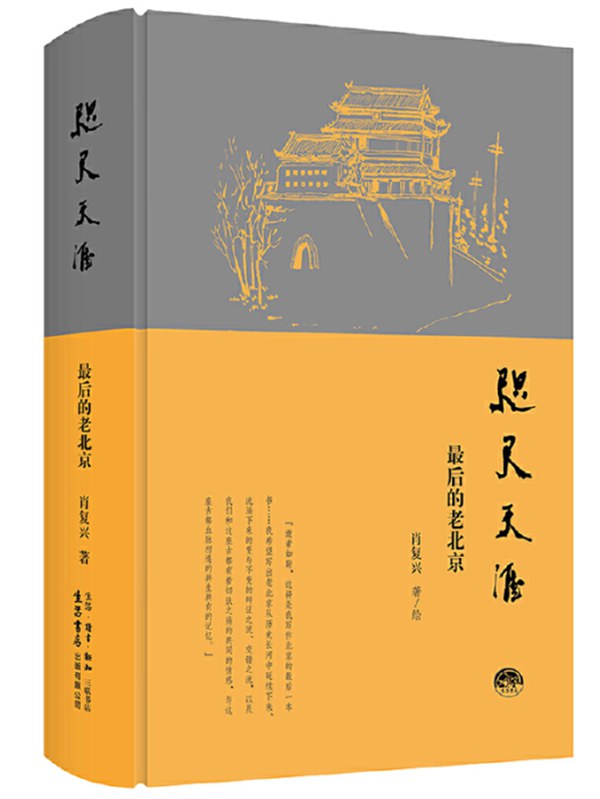 1930年,林志钧先生为陈宗蕃《燕都丛考》一书写序,开端先借题发挥,说他曾经住过的宣武门外“老墙根地旷多坎陷,其接连上下斜街处,则低峻悬绝,考辽金故城者,辄置为辽南京金中都北城墙址。”随后历数上下斜街曾经的名人居处,接着又写了一段,讲下斜街的土地庙:“庙每月逢三之日,则百货罗列,游人摩肩接踵,与七八两日之西城护国寺、九十两日之东城隆福寺,同为都人趁集之地。” 读这些文字,可见得林先生对老北京的熟悉,更可见得林先生对于老北京的感情。这确实是只有对老北京非常熟悉并具有深厚感情的人,才可以如数家珍说出的话。林先生的这番话,让我想起清人黄钊当年目睹这段辽金故城时写下的诗句:“辽废城边可放舟,章家桥畔想经流,百年水道几难问,空向梁园忆昔游。” 如今,还有多少人留心诸如宣武门外章家桥、梁家园这些老街巷变迁的历史呢?谁还会关心现在宽阔的宣武门外大街曾经有过辽金时代的老城墙根老河道,有过热闹的土地庙,有过那样多的名人故居呢?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路两旁的高楼林立,早已经遮盖淹没了过去的一切。 那天,读戴璐《藤阴杂记》,其中一段写道:“京师戏馆惟天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禄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之座。”不禁感慨那查楼木榜早已不见,北平和平解放后复建的新楼广和剧场也要摇摇欲坠,一直在重修,高高的吊车,一直还在剧场前立着,恐龙骨架一样,不知是在眺望过去的岁月,还是未来的时光。
1930年,林志钧先生为陈宗蕃《燕都丛考》一书写序,开端先借题发挥,说他曾经住过的宣武门外“老墙根地旷多坎陷,其接连上下斜街处,则低峻悬绝,考辽金故城者,辄置为辽南京金中都北城墙址。”随后历数上下斜街曾经的名人居处,接着又写了一段,讲下斜街的土地庙:“庙每月逢三之日,则百货罗列,游人摩肩接踵,与七八两日之西城护国寺、九十两日之东城隆福寺,同为都人趁集之地。” 读这些文字,可见得林先生对老北京的熟悉,更可见得林先生对于老北京的感情。这确实是只有对老北京非常熟悉并具有深厚感情的人,才可以如数家珍说出的话。林先生的这番话,让我想起清人黄钊当年目睹这段辽金故城时写下的诗句:“辽废城边可放舟,章家桥畔想经流,百年水道几难问,空向梁园忆昔游。” 如今,还有多少人留心诸如宣武门外章家桥、梁家园这些老街巷变迁的历史呢?谁还会关心现在宽阔的宣武门外大街曾经有过辽金时代的老城墙根老河道,有过热闹的土地庙,有过那样多的名人故居呢?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路两旁的高楼林立,早已经遮盖淹没了过去的一切。 那天,读戴璐《藤阴杂记》,其中一段写道:“京师戏馆惟天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禄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之座。”不禁感慨那查楼木榜早已不见,北平和平解放后复建的新楼广和剧场也要摇摇欲坠,一直在重修,高高的吊车,一直还在剧场前立着,恐龙骨架一样,不知是在眺望过去的岁月,还是未来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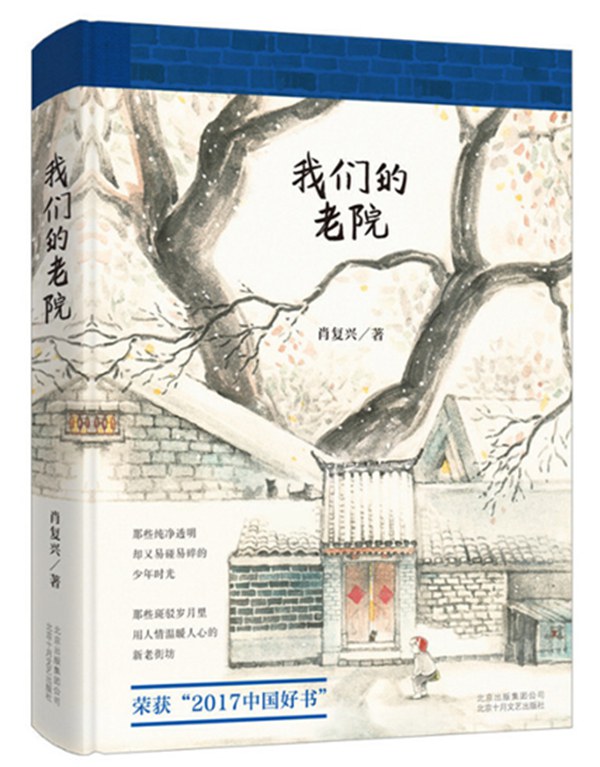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书影
《我们的老院》书影 偶然读到吴梅村和胡南苕关于金鱼池的诗。其中,吴诗:“金鱼池上定新巢,杨柳青青已放梢,几度平津高阁上,泰坛春望祀南郊。”胡诗:“日射朱鱼吹浪泳,花随彩燕扑帘飞。”想起《帝京岁时纪胜》里说金鱼池“池阴一带,园亭甚多。南抵天坛,芦苇蒹葭,一碧万顷”,更有棋罢不觉人换世之感。吴、胡诗中所说的有燕有柳有花有鱼有阁有坛的情景,会让今日人们难以想象;《帝京岁时纪胜》所说的“芦苇蒹葭,一碧万顷”,更会让人以为不那么真实似的。只要看过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就知道不过百年,曾经柳荫鱼影、游人摩肩接踵的金鱼池,早就变成了臭水沟,如今,又已经变成了改造后的居民小区。地理意义上的金鱼池,经过时代的变化、时间的发酵,已经有了历史意义上的新的概念与意义。 如果再看,金鱼池之北有金台书院,之东有药王庙,之西有精忠庙。金台书院旧址尚存,精忠庙却先变为工厂,后和药王庙一起夷为为平地。如今,走在天坛城根下,往北望去,谁还能想象得到金鱼池当年不俗的风光,想象得到金台书院曾有过的书声琅琅,想象得到每年四月药王庙要酬戏于百姓的盛况,想象得到当年北京城唯一一处祭祀岳飞的精忠庙,曾经有过老北京人独特的祭祀方式,“土塑秦桧以煤炭燔之至尽,曰烧秦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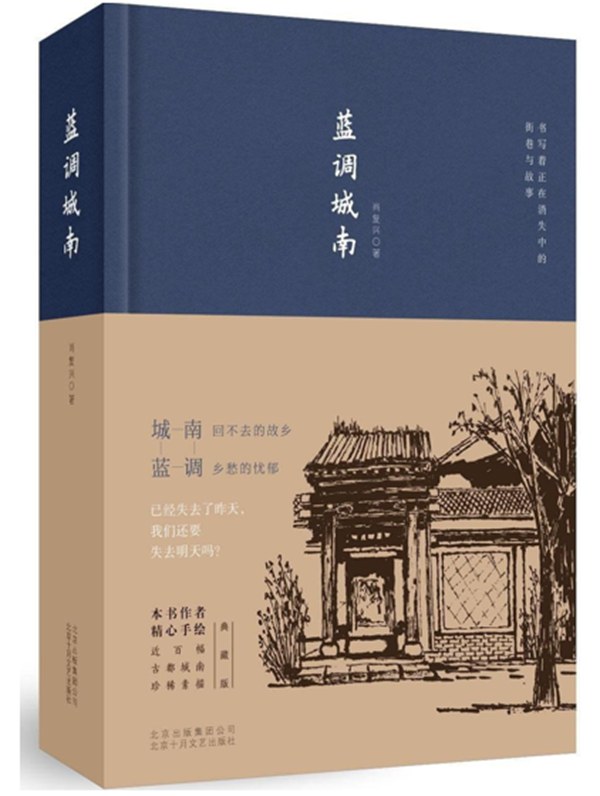
如今,硕果仅存的中和戏院,虽还在旧地,却早就关张,徒存旧名,有尸无魂。庚子大火,中和戏院和大栅栏一条街一起被烧毁,重建时颇费周折。那时,中和戏院是永定门外花炮制造商薛家的祖产,但临街门道那块地方另属他家,要价很高。最后,还是瑞蚨祥的孟老板出资摆平,方才使得中和戏院能够重张旧帜。不是瑞蚨祥的老板心疼中和老戏院而一掷千金,而是那时他正在热捧名伶徐碧云,中和重建之后,孟老板将投资的股份赠送给了徐碧云。这一切戏院内外发生的故事,又有谁记得,谁关心呢?放翁诗说:八千里外狂渔父,五百年前旧酒楼。说是戏楼,也正合适。而今,旧戏楼奄奄一息还在,如孟老板一样的狂渔父早已不在了。
《蓝调城南》书影 如今,走在这些旧地,还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老故事、老传统、老礼数和老地方呢?古诗说:“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更何况经历过漫长岁月的北京,其中的沧桑变化是极其正常不过的。要看到,这些变化之中,有很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会有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这样的变化,多是以历史发展为依托的,而不是想当然的粗暴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古都,不应忘记老北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这些变化之中,要寻找到有规律的脉络,让后人依据历史的罗盘,还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感受到回家的路上扑面而来的浓烈的乡愁。 加拿大学者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了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失去活力。”她特别强调:“必须保留一些各个年代混合的旧建筑。保留这些旧建筑的意义决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在这些建筑上的衰败和失败的痕迹……这些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她说,这些旧建筑“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 而如今走在北京,簇新的建筑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怪诞的建筑强暴地闯入眼帘,全然是一座国际大都市的风范。即使走在旧城老街区,那些雅各布斯所说的“老建筑”“旧建筑”,也已经所剩无几。在破旧立新、维新是举的城市建设观念作用下,这些“老建筑”“旧建筑”,已经破旧不堪,千疮百孔,并不值钱,命中注定要沦为推土机下的死魂灵,哪里会觉得它们的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是无可复制的,是无与伦比的,是只能继承的城市发展的活力呢?随着这些“老建筑”“旧建筑”的消失,更可怕的是和它们连在一起的记忆,也一并消失,以为新改造完成的城市空间,就是以往老北京历史的倒影和地理的肌理。那么,老北京真的就彻底消失而无可追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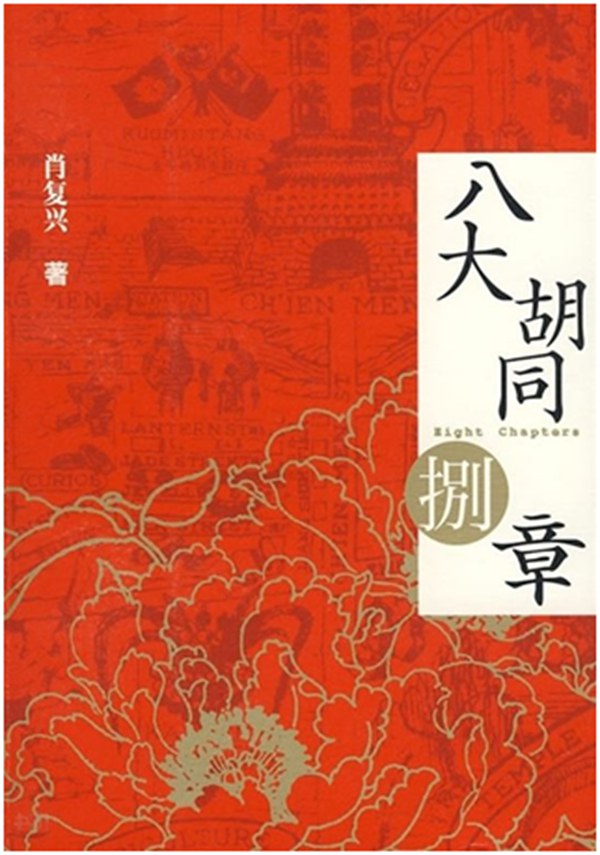 关于老北京的书,我已经写了《蓝调城南》、《八大胡同捌章》、《我们的老院》等几本书,却依然希望以一已残存之力,顽强书写老北京,这便是我在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新书《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我一直相信,记忆在,老北京就在。记忆,是能够让老北京复活并显影的最后一道ph试纸。布罗茨基曾经说:“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布罗茨基这句话的意味和针对性,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在飞速变化中渐行渐远的老北京,尤其如此。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这本小书,我不知道能否做到。
关于老北京的书,我已经写了《蓝调城南》、《八大胡同捌章》、《我们的老院》等几本书,却依然希望以一已残存之力,顽强书写老北京,这便是我在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新书《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我一直相信,记忆在,老北京就在。记忆,是能够让老北京复活并显影的最后一道ph试纸。布罗茨基曾经说:“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布罗茨基这句话的意味和针对性,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在飞速变化中渐行渐远的老北京,尤其如此。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这本小书,我不知道能否做到。
《八大胡同捌章》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