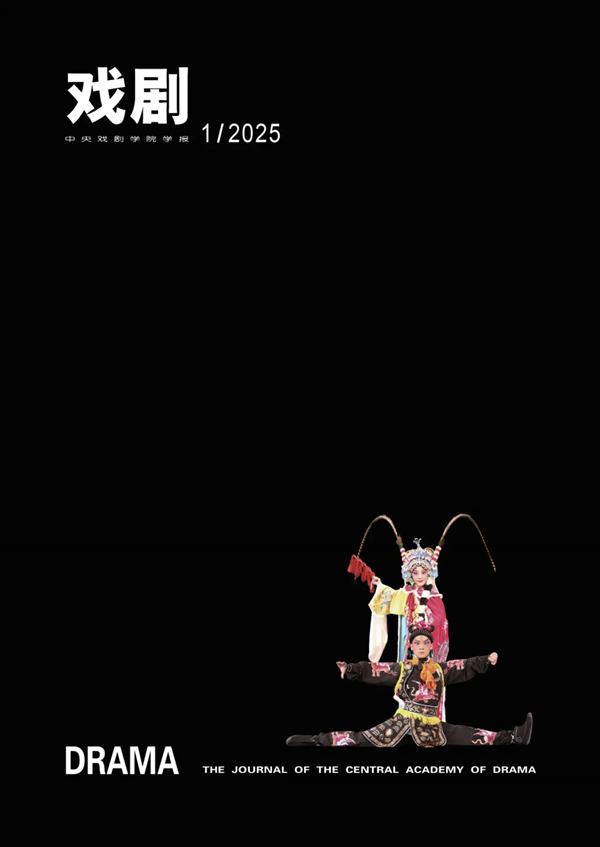
2022年无疑是俄罗斯历史上非凡的一年,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斯坦尼体系”或“体系”)的发展史而言,也是一个非凡的节点。本文从2022年俄罗斯出版的几种新书和两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入手,回顾斯坦尼体系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
一、斯坦尼体系的整体性及命运问题
2014年,俄罗斯学者И. Б.玛洛切芙斯卡娅(Ири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алочевская)在她的专著《托甫斯托诺戈夫的导演流派》(«Режиссерская школа Товстоногова»)中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遗产的命运是如此复杂,有时甚至是戏剧性的,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十年过去,这句话还是很有分量。值得我们深思。
2022年,有一部出版的新书对戏剧体系的命运问题作了论述。这就是里亚波索夫(Ряпо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Юрьевич)的《20世纪俄罗斯导演艺术:体系、流派、概念、思想》(«Русское режиссер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20 века: системы,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и, иде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22)
该书在序言部分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塔伊罗夫的戏剧体系,瓦赫坦戈夫的“游戏戏剧”体系和米哈伊尔·契诃夫的表演方法。此外还概述了20世纪俄罗斯其他著名导演的戏剧观念和舞台艺术成就。里亚波索夫谈到戏剧体系的命运。他写道:
没有首创者关照的戏剧体系,就像没有主人管理的房屋一样,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它们会恶化并逐渐崩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苏维埃国家竭力支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将他塑造成戏剧先知,把他的“学说”塑造为不容置疑的戏剧教条,但是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完整著作的体系并没有保存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们在不同年代与他共事,分别面对演员自我修养和角色创造方法的不同发展和演变阶段,掌握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所掌握的技巧和方法。与此同时,他们每个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舞台方法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本身。当对“体系”的修改越来越多时,结果也就很自然了。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与他共事的M. H.克德洛夫和M. O.克涅别尔继续了他们老师的实验,但克德洛夫版本的“形体动作方法”和克涅别尔的“行动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对体系的修改却相去甚远。反过来,A. B.埃弗罗斯和A. A.瓦西里耶夫“第一手”直接从克涅别尔那里获得的小品方法,由于以不同的方式用于不同的目的,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方式修改。
上面几段文字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这样图画:一方面是戏剧体系“变得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体系修改版彼此相去甚远”的;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舞台方法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本身”,在俄罗斯形形色色的表演工作坊、大师培训班,几乎全都如此,没有例外。
这种局面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例如,2019年在《前沿论文》(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第4期发表了纳金科(М.К.Найденко)等三人的论文,题为《现代戏剧学派完整性问题》(«Проблема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атральной школы»)。作者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其主要核心以及社会文化基础是对艺术,尤其是戏剧的崇高道德目的的信念。尼古拉·果戈理曾热情洋溢地论述剧院是“一个讲坛,在这里你可以对世界传播关于行善的理念”,半个多世纪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样动情地指出:“这个讲坛落入了人类败类的手中,他们把它变成了腐败之地。”
文章突出了体系的“主要核心”是要求剧院重视传播崇高的道德信念,成为对世界传播关于行善理念的讲坛,这是从果戈理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延续下来的俄罗斯文化的传统。这篇文章明确地强调只有不忘体系的主要核心,才能确保“现代戏剧学派的完整性”。
上面提到的玛洛切芙斯卡娅的著作《托甫斯托诺戈夫的导演学派》早就指出:
惋惜的是,即使在今天,功利主义的态度也常常扼杀这一体系的精髓。这些体系的解释者仍然仅仅将它看成一种技术(технология),而它却是一种具有强大伦理基础和崇高道德目标的整体文化的一部分。
可见,里亚波索夫的担忧不是个别人的担忧,维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完整性是俄罗斯戏剧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特别注意梳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三位不同类型的优秀学生的微妙关系。他们当中有远离俄罗斯、在欧美传播发展了斯坦尼体系的米哈伊尔·契诃夫,有突破斯坦尼体系的体验派框架而选择表现派表演方法、自创了“幻想现实主义”的瓦赫坦戈夫,有长期陪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忍辱负重,为“体系”著作的撰写贡献了自己智慧的杰米多夫。
其实,除了这三位,还有早年摆脱斯坦尼的思想束缚而离开剧院,后来与斯坦尼论争长达40年,最终在“反对形式主义”的重压下回归老师怀抱的天才导演梅耶荷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背叛”自己的老师,创造自己的新流派新方法,对世界戏剧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他们都不忘自己的“根”在什么位置,他们尊敬老师,保护“体系”,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感人的。
2024年6月7日,俄罗斯专家谢尔盖·切尔卡斯基(С. Д. Черкасский)在北京演讲时做了一个比喻:门捷列夫逝世后,他发明的元素周期表增添了许多新元素,这并不会否定元素周期表的价值,只能产生更加巨大的价值。同样的道理,斯坦尼的学生为体系增添了新方法、新流派,这是体系的发展,是好事。对于体系的发展逻辑,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例如,以杰米多夫命名的表演流派实验室(Актерская Школа-Лаборатория им. Н.В.Демидова)声称:“杰米多夫本人写道,他的技术诞生于体系的深处,假使没有体系它就不可能存在。”
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巴尔马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рмак)教授在他出版于2022—2023年的《论方法论与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其他人》(«О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 школе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и другие»)一书中写道:“契诃夫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一路走来—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才能将他的惊人发现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对比。他夸大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某些方面,正如他夸大了自己作品中的许多东西一样。契诃夫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演员,一位杰出的戏剧教师,他用许多真正无价的发现丰富了方法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他甚至超越了我们通常对天才的理解。契诃夫喜欢的东西,他的方法的许多追随者却不喜欢。但不仅仅如此。要正确理解契诃夫,就必须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
这话说得好!“青于蓝而出于蓝”,斯坦尼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都有胜于老师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不忘记自己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一路走来”的。他们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自己的方法,并没有损害老师首创的体系,“体系”的整体性由于增添了新的方法和学派而更加巩固和有力了。
二、弥补缺憾,斯坦尼体系进入“克涅别尔时代”
(一)斯坦尼体系成书过程中的缺憾
一种戏剧体系要讲授、传播,诉诸运用,必须将其内容写成书本。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演员自我修养》《演员创造角色》等书稿,直到他病入膏肓之际还没能印制成书,而他重大的新发现要补写进书也为时太晚。这个颇大的缺憾之所以酿成,客观上和书稿遭到严格检查有关,主观上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完美主义心态在起作用。
1.“瑜伽”及一批重要术语的删除
关于“瑜伽”一词的删除,切尔卡斯基的专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瑜伽》(«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и йога»,2013)讲得最为清楚详细。据切尔卡斯基披露,在20世纪 3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成为必受检查的对象。自 20 年代末以来,莫斯科艺术剧院就被强行改造成一个“模范剧院”,一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塔”,还成立了一个“读本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очтению книги»)—“所有不符合唯物主义哲学和二元论要求的东西都要从手稿中删除”。
“瑜伽”一词,还有其他可能被认为不符合唯物主义的字眼,都会是需要删掉的对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在1930年写给古列维奇(Любовь Яковлевна Гуреви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要危险在于‘创造人类精神的生命’(不准谈论精神)。另一个危险是:潜意识、发光、受光、灵魂一词。他们也许不会因此禁掉这本书?”
切尔卡斯基引用“莫艺”档案,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自我编辑”(заниматься вынужденной саморедактурой),几乎所有提到瑜伽的地方都被划掉,“普兰纳”(prāṇa)一词消失了,“情感记忆”一词被“情绪记忆”取代。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戏剧艺术的笔记中甚至找不到“精神”一词,因为这个词面临着审查禁令的威胁……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为了通过审查而在用语上做的妥协。
因此,正如德波夫斯基(В. В. Дыбовский)所写的那样,“今天所感受到的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思想的歪曲……可能在该书出版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根据斯梅良斯基(А. М.Смелянский)的说法,如果要了解1938年俄文版的文本是否充分表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必须重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的三个连续版本,即1930年版(当时古列维奇尚未加入编辑工作)、1932年版(她拒绝继续工作之后)和1935年版,后者是美国版《演员自我修养》的基础”。
2.新的发现未能写入斯坦尼的著作
除了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进行严格的检查之外 ,阐述“体系”内容的书籍出版久久地滞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实践中得出了关于演员创作的新结论和新概括,这迫使他果断地重新考虑对演员的教育方法,以及创造角色和表演的过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其体系形成的不同阶段发现并研究了演员创作的一系列要素,并将其归结为一个概念—动作。但是,这里说的“动作”已经是心理-生理性的有机整一的过程。过去,动作被看作与体系的其他元素,例如注意力、想象力、真实感、交流、节奏、言语等并列的关系,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即体系形成的最后阶段,这些元素开始被看作动作的必要条件,是行动之中有机地固有的元素。但是,遗憾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中并没有反映出对动作的新理解。托甫斯托诺戈夫在20世纪 50—60年代之交已经对此下定了最精确的定义,表达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0世纪30年代的最后想法:“行动是在与小圈子中的特定环境斗争中实现目标的统一心理生理过程,并以某种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中表现出来。”
晚年的实践经验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得出结论:不可能分别创造内部和外部的感觉。“只有在对剧本和角色的生活有真实感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创造性感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6年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且颠覆性地重构了整个排练过程,此后不再首先谈论角色的心理,而是将身体的探索作为理解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的主要和起始方式。
当然,这种排练方式与他正在撰写的这本书的构思、观念必然发生冲突。尽管如此,此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确定:不可能将体验过程与体现过程、外部与内部分开。过去他主张“演员在创造性的体验过程中的自我修养”(«работа актера над собой в твор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живания»)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内在的舞台感觉,这种感觉与真实的身体感觉、与演员完整的舞台存在是互相隔离的。(尽管是假定性的,但毕竟隔离了!)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毅然地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再次面对创造性的碰撞,这种冲突比他过去任何一次在演出中的失败更痛苦和悲惨。切尔卡斯基在谈到这一次“碰撞”时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中获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为舞台发现了自然法则—身心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规律,并在实践中检验了这一规律,从容地从理论上思考这一规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意识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即使在结构上也没有反映出他最终知识的精髓!”
3. 病入膏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病床上竭力改书稿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比任何人都明白,已经交付印刷的著作中并没有反映出他对动作的新理解。重新写书绝对不可能,但如果不修改,他的著作将无法反映他当前对表演艺术的新发现。
他陷入了“莎士比亚悲剧般的选择”。
最后,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演员自我修养》的最终打字文本寄往美国;俄文版书稿继续修改,试图在写成的文本中规定创造性自我感觉的每个要素的行动属性,演员心理生理过程的完整性,演员在舞台上创作行为原则上的不可分割性。
中国读者可以在《演员创造角色》中译本(8卷本第4卷)看到正文后的注释中所补充的文字。例如,561页的第37条注释:
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于“从内到外”的公式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他得出结论说,按照心理与形体、内部与外部相联关的规律,不仅仅内部可以激起外部,而且外部也可以影响内部。他从这条规律得出了一个对他说来十分重要的结论:从外部出发,可以最容易不过地去掌握内部。“对于演员不能马上感觉到的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可以不从内到外,而是从外到内去接近。这条道路我们在创作初期走起来比较容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跟可以看得见、可以触摸到的身体打交道,而不是跟不可捉摸的、变化无常的、韧性执拗的情感和内部舞台自我感觉的其他元素打交道。我们以形体与精神生活中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基础,以他们的相互影响为基础来创造角色的‘人的身体’的线,为的是通过这条线而自然地激起角色的‘人的精神’的线。”(见本卷第387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人的身体”的线首先是指人的动作和行动的逻辑,通过这种逻辑,最容易深入形象的内心世界,并且掌握这个内心世界。“如果是真实地做着什么,那就不可能按照别的样子去感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断定。
虽然无法重写经过严格检查的正文,但是,用类似的注释分布于正文之后,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新发现未能写到书中的缺憾。
(二)斯坦尼体系进入“克涅别尔时代”—巴尔马克推出新观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后,他的学生积极地将老师已经发现的苗头或者新的方向,进一步地深化、系统化、理论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无论是与歌剧-戏剧工作室的学生一起学习,还是与艺术剧院(由克德洛夫执导)的演员一起排练《答尔丢夫》,或是指导克涅别尔(M. O. Кнебель)的工作,他都强调排练工作的不同观点,强调演员在创造角色上的不同方法,这既是基于他所有创作经验的总和,又是基于他对“动作/行动”的新理解。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没有为他最后的思考和排练方法的试验确定一个确切的名称。他逝世后出现的术语—形体动作方法、行动分析法和小品方法,都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提出的(形体动作法概念是克德罗夫提出的,行动分析方法是克涅别尔提出的),而且,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也是后来才逐步阐释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后,他的学生当中最优秀、对体系发展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克涅别尔。
巴尔马克的《论方法论与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其他人》书中有一段话:
在俄罗斯,导演学派与演员技巧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缔造的。在他们逝世后,这个学派率领并继承他们的事业的,是玛丽娅·克涅别尔。因此,我们知道,我国的戏剧理论和戏剧教育有两个时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代与他逝世后的克涅别尔时代。
巴尔马克书中第六章的标题是:“克涅别尔的时代”。巴尔马克是克涅别尔亲手培养起来的学生,他认为俄罗斯戏剧理论和戏剧教育可分为斯坦尼和克涅别尔两个时代,这也许和他特别敬爱克涅别尔有关,然而,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遵循巴尔马克的逻辑,“体系”的发展史同样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体系”的“斯坦尼时代”当然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逝世为终结,而“克涅别尔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怎样理解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克涅别尔和克德罗夫都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莫艺”)的导演。克涅别尔在“莫艺”的工作室和剧团的时间是1918到1955年,其中,1932年起从事戏剧教育工作。克德罗夫从1922年进入“莫艺”的工作室,两年后进入“莫艺”剧团。他在“莫艺”最后一部导演作品是在1968年。他1963年起任苏联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因为长期患病,于1972年逝世。克涅别尔活到1985年,享年87岁。她的非凡贡献载入了史册,当年她的遭遇却是令人难忘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几个“莫艺”老人离开人间之后,中年一代应运而起,顶起大梁,首先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克德罗夫。他曾在革命题材《铁甲列车14-69》和《面包》《死魂灵》《敌人》等重要剧目中扮演角色,大获成功。特别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亲自关注的莫里哀的《答尔丢夫》中扮演主角并接过导演重担,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创造的新方法,摆脱以往习惯的冗长的体验,直接行动起来,进入排练,结果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一年以后(1939)将该剧搬上舞台,得到高度评价。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未给新的方法命名,是克德罗夫后来称之为“形体动作方法”,从此闻名。全苏剧协请他在讲座上向来自全苏联的戏剧工作者介绍新的方法。克德罗夫于1946年至1955年任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总监兼首席导演。自1955年起,他担任剧院艺术委员会成员,并于1960—1963年担任剧院艺术委员会主席,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曾经四次斯大林一级奖金。1963年起任苏联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众所周知,克德罗夫的形体动作方法与克涅别尔的行动分析法之间有过长期的对立与论争。菲尔什金斯基(Вениам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Фильштинский)在他的专著《开放的教育学》(«Открыт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中对双方的论争作了回顾和分析。
菲尔什金斯基认为:
在我们这个时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应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是身体存在作为我们心理生理学的第一要素而与心理不可分割的学说(形体动作方法)。
第二是对剧本中的生活进行事件分析,这是导演最重要的工具(行动分析法)。
第三是演员创作的小品方法(或者小品路径)。
那么,在这三种方法的关系怎样理解呢?
谢尔盖·切尔卡斯基在他的大书《演员的技巧》(«Мастерство актер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 Болеславский — Страсберг: История. Теория. Практика»)第九章的《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节中写道: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也没有为他最后的思考和排练试验确定一个确切的名称。今天,我们使用他去世后出现的术语—形体动作方法、行动分析法和小品方法(途径-подход)。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提出的(形体动作法—M.Н.克德罗夫,行动分析法—M.O.克涅别尔),每种方法的合理性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尽管这三个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它们各自的本质却没有统一的认识。1989年,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新版文集第二卷出版之前,斯梅良斯基写了关于形体动作方法的文章,但从未使用行动分析方法一词,认为它们是同义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语言教学》(«Учение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о сценическом слове»)一书的作者加连杰耶夫(В. Н. Галендеев)也没有将这两个概念分开。
克涅别尔提出了“行动分析方法”这一术语,并与克德罗夫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后者在实践中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简化为最简单的身体动作。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些概念分开。托甫斯托诺戈夫认为形体动作方法是行动分析方法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形体动作方法是行动分析方法的工具”。
与这两个概念有着复杂关系的是小品方法。克涅别尔认为,小品是行动分析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该方法的第二部分—身体探索—有关。托甫斯托诺戈夫和苏里莫夫虽然在必要时使用了小品,但他们认为行动分析方法的精髓不在于小品,而在于无处不在的行动思维。苏里莫夫指出了其中的困惑:“顺便说一句,这仍然是一个荒谬误解的根源:如果在排练过程中做了小品,就意味着导演是在按照‘行动分析方法’工作。荒谬!可能有小品,也可能没有小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方面!”事实证明,行动分析法的精髓不在于小品,而在于行动思维。
Н. В.杰米多夫的追随者认为,有必要将小品方法分离成一个独立的概念,而不是将其与行动思维严格地联系起来。这一体系发展方向的口号可视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与佐恩(Б. В. Зон)的谈话中表达的论点:“通过小品,你记住了生活”,这为发展各种小品类型、创造小品排练哲学提供了无限可能。
无论如何,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前最后的发现,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关于行动分析方法、形体动作方法和小品方法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仍未解决。值得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心灵探索与身体探索之间的关系、动作与情感记忆之间的关系、先验的导演认知与小品分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着阿德勒与斯特拉斯堡之间的长期争论,这是演员创作中感性与理性之间永恒争论的一个特殊案例。
今天,关于行动对晚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重要性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在许多戏剧和戏剧教育的实践者例如克涅别尔、托甫斯托诺戈夫、波拉米舍夫,苏里莫夫,赫伊菲茨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证。
显然,切尔卡斯基的观点比较客观,认为三种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作为克涅别尔嫡系学生的巴尔马克的观点就比较鲜明,他在《论方法论与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其他人》一书中写道:“假如玛利娅·奥西波芙娜在艰巨的斗争中坚持行动分析法,始终强调方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方法不会覆盖整个体系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部学说,而是在新的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再说方法就是方法,不是什么完美之中最完美因此正要停滞的东西;方法不是探索和发现的终结,而是正在奔向未来,那么,玛利娅·奥西波芙娜的对立面就会宣布形体动作法是苏联戏剧唯一的可靠的方法。”
巴尔马克毕竟是比切尔卡斯基年长不少的老教授,他将斯坦尼体系的“当代”称为“克涅别尔时代”,干脆利索,显得爽快。他在下面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玛利亚-奥西波芙娜创造性精神生活的壮丽抛物线,她朝着自己的目标,朝着她的教学、导演和理论著作的最高任务—在俄罗斯戏剧界建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学派,使之稳步前行,避免那些对“体系”不懂装懂的追随者和当局的官僚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活的思想变成教条,“体系”必须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更新、永远富有成果的戏剧思想。
用杰出的波兰教育家和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话来说,她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个答案。
克涅别尔与克德罗夫的分歧矛盾应该说解决了,斯坦尼体系的“当代”就是“克涅别尔的时代”。
三、研讨斯坦尼体系的发展史—2022年莫斯科的两个会议
2022年3月和11月,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ГИТИС)先后举办了研讨斯坦尼体系的学术会议。两会相隔仅8个月。3月份会议的目的是回顾形成于1939年的列宁格勒戏剧学派与“行动分析方法”的关系;11月会议的主题是“在白银时代背景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东方的影响”。
(一)2022年3月会议:对行动分析方法和小品方法的历史总结
克涅别尔在俄罗斯戏剧史上的地位获得提高的又一个证明,就是在2020、2021、2022三年内连续举行了三届“克涅别尔报告会”(«Кнебел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为历史上的一个戏剧导演兼教育家如此密集地召开学术会议,不仅在俄罗斯,即使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
三届研讨会的主题都不同。第一届的题目是“小品与学派”,第二届题目是“传统、学派、方法论”(Традиции, школа, методология), 给人的感觉是2022年的第三届最重要和深入。会议主题是“行动分析方法与列宁格勒戏剧学派:第三届克涅别尔报告会”(Методология «действе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 наследи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театральной школы: Третьи «Кнебел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明确指出要回顾形成于1939年的列宁格勒戏剧学派与“行动分析方法”的关系。会议由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巴尔马克主持。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学派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通过视频出席了这次盛会。他们是圣彼得堡的菲尔什金斯基、科洛托娃和波哈第列夫。菲尔什金斯基是俄罗斯国立舞台艺术学院表演系主任,其专著《开放的教育学》影响很大。2022年又出版了《戏剧教育学:日日与年年》(«Театральн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Дни и годы»)。科洛托娃(Наталья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Колотова)197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戏剧、电影与音乐学院,后来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学术剧院,出版了一本佐恩的日记集《教学服务》(«Учить служению»)。
什么是列宁格勒戏剧学派的特点?谢尔盖·切尔卡斯基在2004年(学派形成65周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列宁格勒学派无疑是以戏剧方法理论为导向的,它建立在对剧本结构、表演的实质、艺术形式的详细了解之上。从对舞台行动的具体观察到戏剧体系的理论,直接导致了意义的扩大,从特殊到一般。”这段话似乎是克涅别尔的写照:从具体的事件、行动的观察入手,逐步上升到掌握作品的全部,她就是走了这条路。而第三届报告会聚焦的问题,就是克涅别尔的“行动分析方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主持人巴尔马克教授发言时提醒大家,“克涅别尔报告会”的目的是展开以舞台方法论为题的对话。他认为舞台方法论正处于低潮期。新一代导演认为过去毫无意义—“反正戏剧从我做起”。如果不仅是导演,连戏剧教师也这样想,那这种误解就更加危险。
报告会回顾了舞台方法论的历史,它起源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瓦赫坦戈夫、梅耶荷德和波波夫的导演和教学工作;克涅别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戏剧流派的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发展。列宁格勒导演和教师佐恩(Б.В.Зон)、托甫斯托诺戈夫(Г. А. Товстоногов),卡茨曼(А. И. Кацман)等人在20世纪50—80年代的作品构成了俄罗斯戏剧史上杰出现象—列宁格勒戏剧学派的基础,该学派在圣彼得堡生存发展至今。
菲尔什金斯基在题为《列宁格勒戏剧学派和M. O.克涅别尔的小品方法》(«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театр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и этюдный метод М. О. Кнебель»)的报告中说,他和克涅别尔在方法和概念问题上有过争论,甚至提出要评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克涅别尔在排练策略方面的不同方法。菲尔什金斯基在书中写道,如果按照克涅别尔的说法,在对剧本进行初步分析之后,就开始进行剧本的“拆解”,并在“拆解”之前进行“情报侦察”,那么,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前的说法,就是“明天请演出”,意思是小品成功后即可演出。初步侦察与心灵探索不是由演员,而是由导演完成的,他有备而来,但暂时沉默;到第一次小品开始时,导演给一个任务,让演员沉浸于剧中,在小品测试的帮助下,唤起他对作品的题材着迷和兴奋。按照菲尔什金斯基的说法,这就是小品方法的开端。
菲尔什金斯基在报告中提出,有必要拓宽 “小品”一词的含义。虽然克涅别尔将即兴文本小品作为行动分析方法的核心,但小品方法是一个更普遍、更深刻的概念:小品不仅建立了演员与文本的联系,也建立了演员与生活的联系。因此 “小品”的概念也包括“前生”(преджизнь)、“传记”(биография)、“联想”(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е)、“每日行动路线”(линия дня)、“风格”(стиль)、“耦合”(сцепка)、“诽谤性小品”(этюды-наговоры)、“杰米多夫式小品”(демидовские этюды)。克涅别尔并不否认小品的多样性,但她认为带有即兴性文稿的小品是其创作的核心。她称小品是演员和导演的排练技巧,但菲尔什金斯基认为,它是一种演员的创作方法,是对演员才华的考验,而不是对剧本作者文本的检验。
菲尔什金斯基表示不赞成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断定“话语是演员创作的王冠”的观点。按克涅别尔的说法,小品是通过演员的话语而成的台阶。小品并不只是为了掌握文本,它还是为了神经、悲怆、情节?为什么话语是表现演员形象的主要手段?还有场景、停顿、呼吸、节奏、眼神、肢体(мизансцена, пауза, дыхание, ритм, глаза, тело)?菲尔什金斯基提出了上述问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小品方法就不是基础,不是演员和导演的哲学,而只是掌握作者文本的排练方法之一。
巴尔马克发言,对菲尔什金斯基思想的创新表示敬意,并阐明了他在老师克涅别尔那里理解和应用的“行动作分析方法”和“小品方法”的含义。他强调这些收获都是概括并继承了克涅别尔的创造性探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建议不要光用头脑分析剧本,还要用行动分析。所谓“行动分析”是通过行动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演员不是分析行动,而是用行动分析(актер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не действие, а действием),也就是他用身体,用心理生理学方法检测他在舞台事件中的行为逻辑。在“行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挪用”的目的,即把角色的文本变成自己的。如果表演者不在小品中检查角色的逻辑,他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在问了自己“在这个事件中我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之后,演员将角色的逻辑变成了自己的逻辑,而在小品之后,他仍然会回归剧本中,回到 “餐桌时代”,因为别人的逻辑,人们可以在餐桌上无休止地谈论,而现在,当事件和行动经过“脚”的检验之后,就变成了个人的逻辑。
菲尔什金斯基在报告中把话题转向佐恩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1933年到1938年间,他曾经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做了记录,他的《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会面》于1955年出版,于2011年再版。书中记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3—1938年间寻找并制定排练规律的情况:他身患重病,但思维特别敏锐,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来得及说出来。佐恩记录下来,功劳巨大。
在佐恩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有力表述:“今天我们阅读,明天请演出”(« Сегодня читаем, завтра пожалуйте играть »),可谓掷地有声。菲尔什金斯基认为,这些话是对“小品方法”的赞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使演员与作者之间直接联系,而不是以导演的“智慧探索”为中介。至于文本,演员通过“小品”(этюд)寻找行动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接近文本。对于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说,片断和任务(куски и задачи)并不具有上述意义,“直达”比任务更容易,“小品”比预先的分析更有效,因为演员通过直觉记忆,而思维使任务固定下来。演员最重要的是“投入生活”!在《塞维利亚理发师》的排练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说:“运用小品,我们能够回忆起生活。”应该一辈子这样做。
菲尔什金斯基在报告的最后引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最后一次排练时说过的一句话:“只有一条路,其他的都是垃圾。”这条路就是在舞台上寻找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佐恩的回忆与研究是第三次克涅别尔报告会的一个重点,他是晚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目睹和记录者之一,成功地奠定了他学派的基础。他相信小品,并将自己培养演员的方法建立在循序渐进和多样化的小品探索之上。
尼·阿·科洛托娃的报告《鲍里斯·佐恩的教学原则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Бориса Зона и систем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顺理成章地延续了菲尔什金斯基的观点。她在发言中引用了她的老师、现代俄罗斯导演和戏剧教育学的重要人物多金(Л. А. Додин)的话:“学派的动力来自一致性和信仰。”正是这些品质—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信仰和应用其方法论发现的一贯性—决定了其教学体系。多金在1961—1965年学习的课程成为列宁格勒戏剧学派创始人佐恩教学法创新的顶峰(佐恩于1965年逝世)。
佐恩在1933年就已经是列宁格勒著名导演与教育家,他开始定期去莫斯科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课,向他提问,在实践中与自己的学生和青少年剧院的演员核对答案,然后带着新问题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38年8月逝世。佐恩是列宁格勒唯一见证了“形体动作方法”诞生的导演和教师,他继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后的教诲,并先后将其体现在自己的实践中。
根据他在日记中的自述,早在 1927 年,他就开始着手创建一门“在方法论上经过验证”的课程(«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 выверенный курс»),其中的发现和发展至今仍被沿用。
第三届克涅别尔报告会表面上没有始终聚焦于克涅别尔一人,但却通过列宁格勒学派的研究,体现了克涅别尔的方法论并非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必然现象,它生动有力地体现了“体系”发展的逻辑。
(二)2022年11月会议:斯坦尼体系研究的新趋势
只过不到八个月,2022年11月2—3日,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又召开一次有关斯坦尼体系的学术会议。主题是“白银时代背景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东方的影响”(«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в контексте эпохи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влияние востока»)。这是一次有外国专家参加的全俄规模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级别比第三届克涅别尔报告会要高,议题超越了小品方法、行动分析方法等具体问题。
1.斯坦尼体系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学术界更加重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类学属性。通过艺术学副博士科普捷夫(Л.Н.Коптев)的两篇论文便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一是《演员作为舞台上的人:从人类学视角思考》(«Актер как человек на сцене: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其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角色的人类精神”》(«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духе роли»)。
在前一篇论文中,科普捷夫指出,苏联儿童戏剧的创始人,导演、演员和教育家马卡列耶夫(Л. Ф. Макарьев)教授早就提出了“舞台上的人”这个新概念。简而言之,这个概念是由“演员本身所具有的人的属性”衍生出来的;是舞台思维为了形象的塑造而编撰出来的。马卡列耶夫认为,“舞台上的人”是演员创造性工作的结果,他将自己与角色的特定环境融为一体。我们要考虑的是舞台上的人。
科普捷夫认为,表演艺术的“人学或人类学维度”(Человековедческое ил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актёр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并非新方法。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歌德和莱辛,再到戈登·克雷、米哈伊尔·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同时代的阿尔托和格罗托夫斯基、巴尔巴等戏剧大师,以及许多研究人员,都将当代戏剧学的发展趋述概括为某种“人类学转向”。
科普捷夫在后一篇论文中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人类学视角对演员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演员作为角色扮演者,实际上是“精神—灵魂—肉体”的三位一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来描述角色精神生活的概念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概念有:“神秘剧”(«мистерия»),“天性”(«природа»),“升华”(«возвышение»),“精神”(«дух»),“力量”(«сила»),“创造的灵魂”(«творящая душа»),“深层中心”(«глубинный центр»),“体验”(«переживание»),“真实性”(«подлинность»),“真理”(«правда»),“信仰”(«вера»),“能量”(«энергия»),“行动”(«действие»),“创作的自我感觉”(«творческое самочувствие»),“家园”(«дом»),“准备”(«готовность»)等等。
科普捷夫说,虽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舞台艺术的主要目的是创造角色的人类精神生活,并将这种生活以艺术形式搬上舞台,但是,人类学方法未能及时用于艺术理论。20世纪80年代,关于“体系”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著意义的认知得到了解放。巴切利斯(Т. Бачелис)驳斥了过去“评论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体系”诞生于象征主义戏剧创作的观点,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超意识”(«сверхсознательное»)的接受是非常深刻和严肃的。在1907—1908年的作品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也在寻找 “新的舞台原则”,意图是要将演员“从日常生活的乏味带入精神和超意识的高度”。斯特罗耶娃(М. Н. Строева)在她的专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探索(1898—1917)》(«Режиссерские искания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1898-1917»)一书中确认,在通常的世俗面具背后,能够识别“人类精神生活”的真相,其中潜藏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仰、美学以及“哲学最高任务”。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罗斯人文主义研究开始了对新价值和新意义的探索。索洛维耶娃(И. Соловьёва)将早期莫斯科艺术剧院(MHT)的艺术称为东正教艺术。斯梅良斯基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舞台的灵魂及其牧师兼演员,通过自身传递某种更高尚的力量”。此外,斯梅良斯基还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神化”了戏剧,他将最重要的宗教教条诠释为艺术生活的准则。在他的体系中,很容易找到与“誓言”“谦逊”“服从”等概念的对应关系。巴日特诺夫(Л. Пажитнов)利用哲学工具书发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主张包含着禁欲主义成分,即“将演员从一个滑稽可笑、逗乐大众的喜剧演员提升为先知,提升为一个重视道德内涵和绝对命令的人”。
科普捷夫对论文开头列举的“神秘”“自然”等各种“工作概念”(рабочие понятии)作了解释,最后在论文结尾处写道:……这些概念定义了“角色的前文本精神结构”(дотекстов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рол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包含在文本的诞生之中、这些概念包括:“神秘”“自然”“升华”“精神”“力量”“创造的灵魂”“深层中心”“体验”“真实性”“真理”“信仰”“能量”“行动”“创造的自我感觉”“归宿”“准备”。作为人的演员在创造性准备行动中,成功返回其精神家园,这是贯穿 “体系”的主导元素,似乎构成了其精神范式和角色的精神基础。
如上所述,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确实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这一趋势在2022年全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讨会上显现出来,并不偶然。会议的目的是要确定“白银时代”文化中那些有助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诞生和形成的方面。这个设计反映了文化学、人类学方法在“体系”研究中现身。
俄罗斯学者一直关注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是晚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凌驾于早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上,还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斯梅良斯基旗帜鲜明地捍卫了“体系”的完整性:“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不是把‘体系’理解为一本经书或教科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整体文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他最后的发现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这种文化的背景之中,而这种文化是没有止境的,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这种整体认识,对 “体系”发展的理解不是线性的,不是把后来的发现看成对先前发现的抵消,而是看作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其中包含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探索的复杂性,这对当今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极为重要。
不同文明对话的角度,人类学的角度,都有助于用“整体文化”理解“体系”的发展。在11月召开的全俄的研讨会上的22人发言之中,有超过半数表现出“人类学转向”。下面是从22人的发言中举出的例子:
例一: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库尔古佐夫(А. В. Кургузов)在其题为《瑜伽体系的哲学—起源、原理和在表演艺术中的实际应用》(«Философия систем йоги — истоки, принципы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в актерском искусстве»)报告中强调认知不同瑜伽流派特殊性的必要性。
例二: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斯特雷勒茨(К. М. Стрелец)在题为《20至21世纪瑜伽在印度和欧洲的组成部分》(«Индийские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йоги ХХ–ХХI веков»)的报告中回顾了历史:瑜伽作为一种身体和精神自我完善的练习体系,早在古代印度就已出现,而现代人所熟知的欧洲瑜伽则形成于19至20世纪之交。斯特雷勒茨分析了印度瑜伽、西方对其文化的重新诠释以及在现代戏剧演员培训教育过程中对它的认识。
例三:东西伯利亚国立文化学院(乌兰乌德)戏剧艺术与舞台演讲系主任曼札尔汉诺夫(Э. Е. Манзарханов)在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伦理学与东方教义和实践中的道德规范体系》(«Этик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системы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норм в восточных учениях и практиках»)的报告中,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伦理学与东方各种精神教义和实践中的道德规范进行了比较,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伦理学规范是其体系的组成部分,与东方精神体系和教义的道德原则不谋而合。
例四:孟加拉国达卡大学戏剧与表演研究学院副教授兼俄罗斯国立戏剧艺术学院外国戏剧史系研究员的布扬-阿布尔(Буйян Абул)在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孟加拉国寻根剧场的传统戏剧技巧》(«Система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техник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театра в спектаклях “Театра корней”»)的报告里指出,1990年初,孟加拉国出现了一种 “寻根戏剧”,戏剧从业者探索民间戏剧的原则,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与孟加拉国的传统戏剧艺术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混合戏剧”。
例五: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历史、哲学和文学系教授平斯卡娅(Е. Н. Пенская)在其题为《白银时代卡巴莱歌舞表演剧目中的东方主题》(«Восточные мотивы в репертуаре театровкабаре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的报告中指出,转向东方成了对西方文化实用主义的一种特殊的抗议形式。譬如叶夫列诺夫(Н.Евреинов)把根据中国传统戏剧改编的美国剧本《黄马褂》搬上舞台,成功征服了欧洲。
例六: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科研部首席研究员柯列斯尼科夫(А. Г.Колесников)的报告中探讨了白银时代俄罗斯剧院剧目中的东方主题(Ориентал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альной сцены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例七:伏尔加格勒音乐学院声乐艺术系副教授斯克沃尔佐娃(Ю. С. Скворцова)在演讲中指出,对瑜伽的积极研究使他们理解了斯坦尼体系形成的背景和俄罗斯戏剧学院表演培训发展的特殊性。
例八:普希金国立俄语学院库舍瓦(Г. В. Якушева)教授的报告题目《 安东·契诃夫剧作中的普兰纳》(«Прана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А. П.Чехова»)出人意料,引发了热议。她认为,契诃夫戏剧中的普兰纳(“Прана”)使契诃夫的戏剧将重点从行动的结果转移到了行动的原因,从而偏离了西方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歌德的《浮士德》),走向了分析和沉思的东方。
例九: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历史、哲学和文学系副教授斯克里亚宾娜(Т. Л.Скрябина)在题为 《И. А.布宁散文中的东方和俄罗斯》(«Восток и Русь в прозе И. А.Бунина»)的报告中探讨了白银时代文学中的东方主题。例如,布宁在锡兰和印度旅行后,深深地吸收了东方精神的一些元素:将人与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气的记忆”概念(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прапамяти)、永恒轮回的思想、打破常规生存框架和摆脱生存枷锁的愿望、佛教的死亡解脱思想。
2.研讨“体系”形成的背景、分期与理解
2022年11月的全俄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通过确认斯坦尼体系发展进程分期的统一认识,加强对体系的整体意识。俄罗斯当前最著名的“体系”研究者之一切尔卡斯基在会上做了报告,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背景、分期与理解》(«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 контекст,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осмысление»)。
切尔卡斯基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展逻辑问题:还是该读斯特拉斯堡的书了》(«К вопросу о логике развития системы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ли время читать Страсберга»)一文中尖锐地提出过斯坦尼体系发展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在1910 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情感记忆是演员创造力的基石。戏剧界大多数人认为,斯坦尼体系早期的主导因素是情感记忆,而“体系”晚期的主导因素是行动。在早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刚刚开始探索表演的规律,缺乏经验,难免失误;到了晚期一切都变得正确了。理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摆脱了对资产阶级心理学和情感记忆的迷恋”,“其30年代的练习已经摆脱了里博特唯心主义的光环和瑜伽的神秘主义”。根据这一逻辑,晚期与早期是对立的。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行动思维原则大行其道,斯坦尼体系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Г. А.托甫斯托诺戈夫给“体系”的许多概念下了最准确的定义,用“行动剧场”(«театр действия»)概念取代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剧场”(«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一词。随着时间的流逝,用“行动”的视角观察世界和戏剧表演取得重大成功,戏剧理论和实践开始关注其他要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创作遗产得到了发展,并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在2022年11月研讨会上,切尔卡斯基再次强调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对西方心理学的“情感记忆”学说和东方瑜伽学说有了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充实了自己的专业词汇,并对演员创造性自我感觉的基本要素进行训练,从而形成了“体系”(“体系”一词于1909年出现在他的笔记中)。在演员心理技术领域的发现,虽然是体系形成的早期,但它同时是奠基时期,不仅决定了体系发展的逻辑,而且决定了它的完整性。
切尔卡斯基说,20世纪头十年是重视情感记忆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重视行动的年代,这种时期划分并没有摆脱历史背景的压力,而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观点的演变并不一致。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现代实用教学法,也不可能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遗产与米哈伊尔·契诃夫、杰米多夫的流派以及格罗托夫斯基、斯特拉斯堡等人实践体系的发展接轨。
2022年研讨会没有围绕着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菲里什金斯基教授在《开放的教育学》中所称的“重要的实践概念”(важные для практики понятия),没有纠缠于“形体动作方法”“行动分析法”“小品方法”等舞台实践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而是将斯坦尼体系研究提升到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高度,集中回顾白银时代背景下斯坦尼体系初创期如何到东方(主要是印度)寻找文明源头至今的百余年历史,提高了对斯坦尼体系的整体意识。
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的莎赫玛托娃(Е.В. Шахматова)在会议综述中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借鉴瑜伽教义的一些原则,创造了各种发展和改善演员心理技术的方法。后来,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他的助手、追随者和学生开发出了许多心理形体训练方法,这些方法在演员培养过程中非常有用,并被纳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教学中,被世人称为他的“体系”。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确定“白银时代”文化中那些有助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诞生和形成的方面。
回顾2022年3月和11月的两次研讨会,俄罗斯的斯坦尼体系研究成果丰硕,确实开拓了新的境界,令人欣喜。
结 语
斯坦尼体系博大精深,走过了百余年的坎坷道路,但是,在俄罗斯一代又一代新生力量的持续奋斗下,依然充满活力,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作者陈世雄,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