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反对新名词
原标题:张之洞与新名词

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直隶南皮人。
有关部门禁止外语缩略词如“NBA”、“GDP”等进入媒体,据说是为了“保护汉语”。历史上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是个老话题,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过,“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像火焰那样的语言活力才是更有竞争性的因素;消极地防守、不与外界交流竞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光绪末叶,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报刊等新式媒体开始逐渐兴盛起来。这类大量出现在新书报上的文章,大多有一个有趣的共性,便是喜欢沿用“外来新名词”。而所谓“外来新名词”,又绝大多数是来自东邻日本的汉字借词。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议》,名声大噪,其后便在文章中使用“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等直接来自日本书报的汉字借词。后来湖南人唐才常和谭嗣同办《湘报》,沿用了梁的做法,风行一时。

《时务报》,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藏。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维新派、自立军首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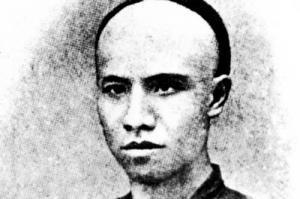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
古文家们十分忧虑惶恐
当时崇尚文风典雅的湖南的古文家们对此十分忧虑甚至惶恐,叶德辉说,现在谈时务的人,常常“自称支那”,而明明可以用“初、哉、首、基”这些字眼的地方,一定要说“起点”。他们不想想,“支那”是当初外来的佛学对“唐土”的称呼,而“起点”是“舌人”(近代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最初往往是不会写典雅书面语的牙行买办等,因此被贱视贬称为“舌人”,大概是说他们只会鹦鹉学舌。)解释西方数学时用的字眼。这些用语要么是翻译过来的词,要么是音译出来的字眼,既不典雅,也不质朴,简直是东施效颦。
叶德辉以“典雅”、“质朴”等传统审美标准来抨击新名词,代表了当时不少士大夫的看法。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不加任何定义与解释的汉字借词仍然通过科举内容改制、考官的喜好等等影响了许多读书人。湖南和江西是风气最盛的,因为两地主持学务的江标、徐仁铸、吴士鉴等,都是对西学西政十分感兴趣的人,政见上也颇为激进。当时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往往被一些考生奉为秘册,希望熟读后,能用新名词来答卷,以投这类趋新的考官所好。1901年,光绪壬辰科(1892年)的进士吴士鉴任江西学政,成了当地所有读书人的大宗师,每年主持考察当地秀才以上生员的岁试(即一个地方生员的学年大考)以及向朝廷推荐“贡士”的贡试等。秀才熊元谔是当时“言西学之第一人”严复的学生,深得严的赏识。他1901年在江西参加岁试时,考官就是吴士鉴。吴称赞熊元谔能模仿梁启超的文风,用新名词答卷,将熊取为第一名。第二年,吴改赴他任,熊元谔参加江西乡试,仍中了举人。显然,喜好熊这种文风的,在江西并不只是吴这一任学政而已。
除了对考生以外,新名词也对一些朝廷的官员产生了影响。吴士鉴的同科进士,江苏武进人张鹤龄很得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任,1902年被延聘为京师大学堂的副总教习,并主持大学堂的招生考试,“各省才隽,一时并集”,实际上掌管了大学堂的全部教学事务。1903年总教习吴汝纶病逝后,他便接任了总教习之职,并延聘日本人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为化学、师范两馆的教习。张鹤龄本人就喜欢“以新词形于官牍”,也就是说不避讳以这类受人攻击的日语汉字借词来写公文。用新名词来写公文,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各地督抚中也有招留学生进入幕府的。1903年,在庚子之乱(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役)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他于1903-1905年之间,曾经拟过奏稿向朝廷建议,将广西的省会移到南宁。据说在这份奏稿中,岑写了“桂省现象,遍地皆匪,南宁为政事上要区,商业上中心”这样的话。后来有人认为,新名词进入呈送最高统治者的奏疏,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类被叶德辉们斥为“不中不西”、“非文非质”的新名词从体制外的报刊文章进入体制内士大夫们的正式文本,似乎已经蔚为潮流。到了宣统元年(1909),甚至在最高统治者的上谕中,出现了“四万万人”这样的提法。据说,起草那个上谕的,是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清廷重臣用新词反新词
对于主要由日语汉字借词构成的“新名词”进入为国选材的科举答卷,甚至官吏文稿公牍,最后甚至是上谕这样一些体制内的正式文本,清末朝廷中的一些重臣是持反对意见的。“满洲第一才子”端方,曾经支持过戊戌维新,事变后因为李莲英与荣禄的保护而未受株连。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立宪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据说,有一次端方在批一位考生的课卷时,写批语道文章“有思想而乏组织,惜新名词太多”,一时传为笑谈。因为他忘记了“思想”、“组织”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
从感情的激烈程度而言,对新名词最为深恶痛疾的是那位在清末倡言“中体西用”,由学务起家的重臣张之洞。张之洞一生开风气之先,在湖北首倡新政,废科举、办学堂,也曾经资助过《时务报》。据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成立学部总管其事。两年后,慈禧太后召张之洞入军机,以相位兼管学部工作,对学部满尚书荣庆形成掣肘之势,这是慈禧一贯的用人之道。张之洞一生仕途的最后一程,便是以中堂的身份管理学务,虽然驾轻就熟,风格则较之早年的“孟浪”而更为稳健。这位张相爷对于新名词的憎厌,在当时流传很广。据说,当时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照例要派京官来相助校对。学部司员们的拟定候选人名单中有留日归国的汪荣宝。这位汪荣宝曾和叶澜在1903年编纂出版过新名词词典《新尔雅》,风行一时。也许,学部司员便是考虑到汪的留日背景及其对新名词的熟悉而作出推荐的。张之洞指着汪的名字说“是轻薄子,不可用”。然后拿起红笔就把这个名字抹了,并回头对满尚书荣庆说,我翰林院难道没有一个人能胜此任的吗?
张之洞看到公牍奏疏这类体制内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词,常常是锱铢必较的,据说一般是立刻用笔抹掉,并注上批语“日本名词!”。后来他自己突然想起来“名词”这个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词,便改注“日本土语”。(江庸《趋庭随笔》)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传说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是说,张之洞有一个门生,要出差去外国,向老师辞行。张问他什么时候启程,他说“办完了出国‘手续’就走”,张说“以后不要用这类新名词”,那个官笑对说,“新名词”三个字也是新名词。(陈英才《两湖书院忆闻》)。另一种说法是,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见拟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路某便半开玩笑半较真地回答说:“‘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这个路某就是路孝植,是路润生的孙子。张之洞默然不语,若有深思,旋即问别人:“路某乃润生之孙耶?”边上的人回答说是,张轻轻地说:“不愧为名人后裔。”张之洞沉默良久的原因,是在默想旧书。如果旧书中曾有“新名词”三字,恐怕路孝植或将受惩,也未可知。
张之洞拒听“亡国之音”
还有些人的遭遇就没有路孝植这样幸运了。有一次一个翰林奉派出国,去见张辞行,说:“到国外见到的情形,随时向中堂‘作报告’。”连说两句,张都不理。来人以为他没有听见,又说了一句。张说:“我不愿听这亡国之音。”更有甚者,有一次学部一个部员进稿,中间有“公民”二字,张立刻“裂稿抵地”,大骂。就是撕碎了稿子扔在地上,口出恶声,显然情绪是激烈到了极点。
曾经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名叫冒征君,字鹤亭。他应朝廷经济特科的考试时,在答卷文章中用了“卢梭”二字。经济特科是清廷自1897年开始推行的一项科举补充政策,目的是让一些研习新学的读书人可以不走八股取士的途径,经由地方学政保举,直接进入中央一级的考试选拔程序。中者称为“经济特元”,如清末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袁嘉谷便是最后一位“经济特元”。这位考生遇到的阅卷考官是张之洞,“卢梭”这个新名词就犯了张的忌讳,因而被贬斥不中。当时都中有人写诗调侃他说,“赢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卢梭。从今卷起书包去,且应明年进士科”。(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又称“张南皮”)
关于这位张中堂厌恶新名词的传闻很多,大多绘声绘色,倒也并非空穴来风。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出《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短讯一条:
闻张中堂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
显然,这位始终极力贯彻自己“中体西用”主张的张中堂,并不只是出于情绪而讨厌人们在公文中使用新名词。禁用亦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好恶。这类来自日语的汉字借词,一般未加任何解释就为人所沿用。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弊端也不是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张之洞也许深切地忧虑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会最终撼倒“中体”。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他百年前的这种忧虑,似亦非完全的杞人忧天。只是,张之洞要求大家“通用纯粹中文”,若连他自己都使用“新名词”三字而不能立刻自觉,又如何能以孤臣孽子之心而遂投鞭断流之愿呢?
(编辑:文博)
| · | 张之洞巧治山西:从整顿吏治和作风入手 |
| ·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慈禧太后比我强多了” |
| · | 维护汉语健康人人有责 |
| · | 没了“WiFi”,拿什么与世界沟通? |
| · | 字母溜进汉语,谁之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