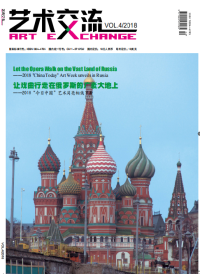“五四”文艺: 斑驳的图景与永恒的话题
艺术交流 VOL.《艺术交流》|胡一峰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但只要我们追索现代文化在中国确立的历史脉络,就不得不重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和逻辑。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艺对后世的影响同样深远。
文艺对“人”的发现
“五四”运动迸发于民族危难、国权沦丧之际,首先是一场唤起人心、救亡图存的运动。但更深层次的看,唤起民众是为了给现代中国诞生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而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而言,“人”的确立又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不乏先进的思想家提出民本、重民等思想,也有如汤显祖的《牡丹亭》这般歌颂人性解放的作品,但并不占主流。封建文化在本质上缺乏对“人”的尊重。因此,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也就成为“五四”时期文艺的重要主题。正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作为一场发现“人”的运动,“五四”的功绩多为亲历者论及。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曾这样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显然,这种刻骨铭心的影响,正是从内心深处生发的自我人格的确立。
即便在一百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中读到前贤真诚而热切的声音。鲁迅在名篇《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并借狂人之口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周作人则极力倡导“人的文学”,并且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要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人”的重视也比比皆是。徐公美在《现代戏剧的意义》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说:“现代戏剧是什么?简单的说一句,就是‘人的戏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文艺家重视“人”的目的是为中国创造一种符合现代潮流的新文明。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看一个国家的文明,需要考察怎样对待小孩子和女人。以此反观“五四”,我们会发现,中国文艺真正从“人”的意义上关注妇女和儿童,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以胡适而言,他通过翻译《玩偶之家》把易卜生主义传入中国,从此,该剧的女主角娜拉成了“五四”时代妇女解放的象征。后来的许多话剧如欧阳予倩的《泼妇》《潘金莲》,石评梅的《这是谁之罪》、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中主人公的身上总映现出娜拉的影子。而在现实中,无数女青年在娜拉那“砰”的一下的关门声中,找到了追求自我解放的勇气和信心,中国的妇女运动面目为之一新。从那时起,把女性塑造为男权附属的文艺作品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时至今日,娜拉的话题依然在讨论女性权益、男女平等问题时不断回响。在当时的音乐界,黎锦晖等人正在关注和倡导儿童音乐。1920年,黎锦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创作完成,此后又创作了《葡萄仙子》《小羊救母》等多部儿童剧。这些作品使用的是儿童熟悉的神话或童话,寄托的则是“五四”时期文艺工作者传播新文化、培育一代新人的热望。
文艺“大众化”确立方向
大众化是“五四”时期文艺的鲜明特征。实际上,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一股文艺大众化的潮流已在酝酿。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要打倒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古典文学,建立平易的国民文学,新鲜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倡导的“美术革命”,实质上也是要建立一种大众美术。文艺要面向民众的思想贯穿了整个“五四”时期,我们可以在多个艺术门类发现其回响。比如,在美术领域,林风眠明确提出:“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高剑父也特别注意艺术大众化,指出:“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艺术是给民众应用和欣赏的。”在话剧领域,郑振铎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的话剧应该是“平民的”,因此“并且必须是:带有社会问题的色彩与革命的精神的”,表现在话剧创作实践上,就是“社会问题剧”在“五四”时期的勃兴。胡适的《终身大事》反映婚姻恋爱问题,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折射伦理道德嬗变,王仲贤的《好儿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困,洪深的《赵阎王》表现了军阀混战的现实。再看音乐界,黎锦晖1920年在北京成立“明月音乐会”,提出音乐会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致力于国乐改进的刘天华也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大众化是一种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发展逻辑,它暗含了理念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方法。白话文受到提倡并在文艺创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就是其中之一。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曾提出,好的文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就是“要明白清楚”。他还说过:“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当时和语言文字关系密切的艺术门类中,来自西方的话剧自不必说,天然地拒绝“之乎者也”的故作高深。在音乐界,萧友梅、黎锦晖、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创作,都运用了通俗易懂、便于理解的白话文。黎锦晖曾这样说:“我也永不能得‘音乐程度较高的鉴赏者’和‘音乐专家’的原谅,因为仍旧不愿尽遵固有的‘乐式’不愿尽配完美的和音;而且‘造词’力求接近普通的白话,‘配谱’力求接近平常的语调,希望歌舞剧的‘歌词’一天天和对话戏的‘对话’相似,台上人‘唱着’和‘说着’一样的明白”。而更直接也更有声势地体现“五四”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或许是民间文艺运动的兴起。正如钟敬文所言,民间文艺运动“是当时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艺家而言,“民间”具有精神家园的意义。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扩展到对“民间”的整体性研究,就像顾颉刚说的,要把埋没了几千年的“民众艺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文学家俞平伯提出“所言浅者所感者深”,呼吁“使诗歌充分受着民众化”“我们要做平民的诗,最要学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吾心归来呀!从人间,归来!”
在后来关于“五四”文艺传统的建构和叙述中,大众化无疑是最强势的声音之一。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到群众中去”。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深入论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以此为基准,规划了中国文艺的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大众化方向则成为国家的文艺方针。时至今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大众”的内涵和“五四”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已有不同,但文艺的大众化依然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具有导航仪的重要意义。
执拗而坚韧的文艺传统
毋庸置疑,“五四”运动带有激烈的反传统色彩,在文艺领域,甚至提出了对传统戏曲的过火批判,将其视为野蛮的“遗型物”。当历史烟云散去,对此又该如何正确理解呢?笔者认为,鲁迅后来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的一段话值得深思。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
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以此体会前贤当时的心态,关于美术革命、批判旧戏的过激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当我们理性而细致地分析这场以反传统为名的运动时,又会发现传统其实以一种执拗而坚韧的姿态融灌其中。发起“国剧运动”的余上沅等人,对待传统戏曲保持了相对公允客观的态度,他们重视戏曲重表现、写意化的艺术特色,并希望能吸收到新戏剧的创造之中。被誉为“中国的舒伯特”的赵元任,作为“五四”时期“新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与胡适、徐志摩等人合作的《新诗歌集》被萧友梅称为“替我国音乐界开一新纪元”。其中,赵元任作曲、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更是脍炙人口,被认为充分反映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的追求,但当我们静心聆听这首名曲时,却会发现主要的旋律素材源于京剧西皮原板过门。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套用一下这句话,或许正因为赵元任使用了对于中国人的耳朵“带感”的旋律,才让这首歌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得到充分张扬。事实上,在赵元任看来,中国传统音乐资源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他在创作中总是娴熟地运用中国民歌、戏曲音乐等元素。
传统对于“五四”文艺的意义不仅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文艺观的传承。一方面,“五四”文艺显示出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另一方面则不动声色地接过了重视文艺社会功能尤其是教化功能的接力棒。中国古人向来重视文艺在成风化俗中的作用——《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论语》早就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论是“诗言志”,还是“兴观群怨”,都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充分肯定。而“五四”时期的文艺家则赋予了文艺改造国民性、唤起人心、塑造新人等多项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本身与传统社会对文艺的要求不同,但重视文艺社会功能并在这种功能铺设的轨道上推动文艺发展的逻辑却是一致的。
关于“五四”文艺可谈的话题还有不少,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中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抑或新文艺创作群体的兴起与现代文艺共同体的形成…… 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文艺丰富而斑驳的图景。但笔者以为,“人”的发现、大众化的方向、文艺传统若隐若现地延续,是这幅图景中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课题。“五四”文艺是一个厚重的历史话题,也是一个深刻的现实话题。“五四”对文艺所提出的课题是永恒的,“五四”文艺对“人”提出的课题也是永恒的,它直接指向并释放了蕴藏在文艺结构最深层之中的张力。
我们知道,回到起点,往往更能看清前进的方向。今天回顾“五四”,重读文艺前贤,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在经典的幌子下走复古的老路,而是回到现代中国文艺起步的地方,考究其内在机理,探查其发展规律,推动中国文艺在古今中西多种资源合力下健康发展。
Copyright © 2011 CFLAC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